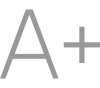陈林
包倬短篇小说集《十寻》收录10篇关于“寻找”的小说,是一组映照不同自我的探索之作。
《红妆》是《十寻》首篇。在《红妆》中,奶奶是个爱美之人,她喜欢化妆,喜欢在镜中再造世界:“只有我和你闲着,心如两块相互映照的镜子。我每天见你坐在镜子前化妆,像是在给自己施魔术。我对比过你化妆前后的样子,判若两人。”化妆前后判若两人,镜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两个世界,化妆所施加的“魔术”改变容颜,镜中之我亦是一个内在之我。这里有双重镜像。“心成为自己的明镜”(波德莱尔《无可救药者》)——奶奶的心与我的心也“如两块相互映照的镜子”。
着迷于化妆是奶奶退守自我的一种方式。她“艰难地寻找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她从外在的世界退守——“他们人多,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又在退守中对抗这个世界,包括社会、学校、家庭所代表的世俗价值观。作为最小的伦理共同体,家庭保存人的群体属性。因此,必须走出家庭,孤绝的个体才会诞生。当带着孙女从家庭出走后,奶奶成了一个无家的人,一个真正孤独的个体,“除了我与你相伴,似乎没有人再走进过你的世界”。现代小说正起源于这种孤独的个体。个体从自然、群体、家庭中剥离,将目光转投自身,于是看见内在的自我。镜中的自我即通过镜面的反射而观看到的内在之我,这是一个内在的人。
在《红妆》中,化妆就像变魔术,“好的化妆师是魔术师”。所谓的魔术,恰恰是现代小说需要释放的力量。在此意义上,现代文学本身是一面镜子,一面照妖镜,或是黑塞《荒原狼》中那个专为剖析自己灵魂的狂人而设的魔剧院。
如果说《红妆》照见自我,那么《亲爱的困兽》《驯猴记》《掩耳记》则是在人与动物之间探寻自我。
某种意义上,人之为人正在于人不同于动物,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在《亲爱的困兽》中,马小明和周虹这对走投无路的情侣犹如困兽,他们置身黑夜,遭遇劫匪,像困兽一样潦倒。但正如在“困兽”之前置有定语“亲爱的”,在无边的黑夜有微弱的火光,在困境中有“我爱你”,小说结尾处写道:“他们甚至忽略了,正悄悄降临的晨光。”这也是晦暗之镜中不灭的人性之光。
应当把《驯猴记》和《掩耳记》放在一起讨论,前者写的是动物的人化,后者写的是人性的动物化,它们互为镜像,彼此叠映,深化了对人性的探索。在《驯猴记》中,驯兽师方小农负责驯一只叫孙小圣的猴子,当把孙小圣驯得“太听话”后,他却感到失望。猴子对人言听计从,动物“人化”了。但人化并没有提升动物性,而是相反,在驯化了的猴子的本性中,照见了人性。在此,动物性不过是人性之镜。方小农带孙小圣逃出动物园,讽刺的是,当他放猴归山,以为孙小圣会逃出樊篱,它却拒绝复归山林,“朝方小农跪下,不停作揖”。不停下跪作揖,动物的“人化”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属于被人驯化了的猴子,也属于人。
在《掩耳记》中,主角苏姗娜上班的公司,作者把它喻为动物园,老板和员工则是不同的动物,他们缺少属于人的精神灵魂。在残酷的丛林法则下,人的缺点暴露无遗。这部小说对现代社会与人性有深刻的洞见。苏姗娜被公司无故解聘,她肩扛仙人掌上班以表抗议。这一意象颇有意味,苏姗娜的行为看似有些滑稽,甚至疯狂,她因此被视为精神病。然而,带刺的仙人掌恰恰代表个性,个性作为工具和武器,其目的是实现现代人的自我保存。因此,肩扛仙人掌的苏姗娜立起了一个典型的现代人的形象。
《生日快乐》《圣诞快乐》写的是新我与旧我的关系,涉及我从何来,往何处等问题。在《生日快乐》中,30岁的朱丽要在家乡给自己办一场盛大的生日宴,以此告别她过去12年不堪回首的生活。对于那段生活,小说较少正面描写,只是暗示那是“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走过的12年。在家乡办生日宴,为了告别过去,迎接新生,却遭父亲反对,乡亲冷落,因为这不符合阿尼卡人的规矩。朱丽此举显得高调,甚至有些造作,但这一仪式对她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如果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告别,她会选择另外一种更轰轰烈烈的方式。”朱丽表达了告别过去的强烈愿望:“从明天开始,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朱丽,像一个新生婴儿,没有过去,只有未来。”这表达的是新我与旧我的断裂,让人联想到米沃什的不一样的理解:“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并不使人难为情”(米沃什《礼物》,西川译)。在《圣诞快乐》中,马小武面对甩不掉的影子一样的过去和看不清的雾一样的未来,他活在弟弟被害的痛苦和悔恨之中不能自拔。与马小武相比,安阳曾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她没有自己的身份,不知所从何来。圣诞之夜,这两个孤独的人坦诚相待,互诉衷肠,彼此照见,在新我与旧我的缠绕中呈现精神的困境。
在这组作品中,《天空之镜》的独特性尤为值得重视——它在人间的多重镜像之外,提供了“天空”的维度,由此探索联结孤独个体的某种真实的可能性,接续了“诗可以群”的传统。《荀子·解蔽》云:“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现代思想是在主客对立中将“天”实体化、对象化,在一种“征服—被征服”的关系中凸显人的主体性,于是切断了天人关联,可谓蔽于人而不知天。
《天空之镜》同样写到镜像的诱惑,也即现代的诱惑,成为他者的诱惑。收音机勾走了男孩父亲的身体和魂魄,女孩的母亲出走了。女孩想去当演员:“她把我们家当成了放电影的幕布,把她当成电影里的人。”这只是又一个逃离的故事,小说笔墨重点不在于此,而在于用儿童之眼、天空之镜观照人间的温暖与忧伤。小说以男孩“我”的视角,写到一块荒着的水田。这块水田像一面明亮的镜子,装着蓝天、白云、飞鸟……或者说水田犹如一只天眼,映照红尘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