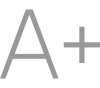主持人陆地(左)和嘉宾禹建强(中)、李映青(右)分享云南国际传播经验。

主持人陆地(左)和嘉宾曹海东(中)、周颖(右)讨论开展数字减贫的国际传播工作。 本报记者 李文君 摄

独龙江乡新貌。 本报记者 陈飞 摄
3月29日下午,2025减贫治理与全球发展(怒江)国际论坛的分论坛“传媒光影·怒江巨变——中国减贫经验的国际传播”在怒江举行。20位来自媒体和国际传播领域的专家们讲述怒江巨变的故事,畅谈以怒江为代表的中国减贫故事如何被世界看见、听见和理解。现场洋溢着媒体光影背后带露珠、切实际、有远见的思考和建议。
记者说
让好故事传得更远
“要致富,先修路”是怒江减贫、中国减贫故事里最常出现的字眼,而怒江减贫故事在国际传播中的“路”也越走越宽。
人民日报社云南分社记者杨文明跟踪报道怒江10年。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独龙江乡的路,没有防护栏,汽车紧贴百米深渊边缘行进。10年后,通往独龙江的路是双向车道、沿途有充电桩,还有不少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自驾游客。除了交通的变化,当地更重要的变化,是怒江的群众更自立、更自强、更自信。杨文明关于怒江蜕变之路的报道频繁见诸媒体,他常常思考:世界上很多地区依然深陷贫困,非常需要中国怒江经验和其他类似经验的启迪。
中国日报社云南记者站站长李映青凭借多年深耕云南国际传播的经验。对于减贫故事的“软着陆”,有很多经历让她记忆犹新。10年来,她跟踪采访了独龙族母女、独龙江乡第一个民宿老板等。她现场展示了一组跨版的彩色英文图片报道,上面有独龙族文面母女10年的对比合照。“视角聚焦的是普通人物的命运变迁,让故事更具人性温度和感染力。”这些具有“无声”力量的报道投放到亚洲新闻联盟的国外主流媒体,借助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实现二次、三次传播,也在国外的纪实摄影展亮相,成功吸引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力扩大了中国乡村振兴故事的影响力。李映青说,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的减贫故事将有更多呈现的可能。
这场活动的主持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周边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陆地听完发言后,用了3组词概括记者们带来的国际传播启示,一是“小而美”,故事即使“苔花如米小”,传播力也能“如牡丹开”;二是“近而真”,熟悉的人身边的事,真诚而打动人;三是“共而散”,能够引起共鸣的人间烟火,才能传播开来。
做出有温度的作品
分享会上,有一对“搭子”在一起合作了整整4年,只为一部有温度、后劲大的纪录片——《落地生根》。他们就是这部纪录片的总导演柴红芳、云南广播电视台摄影记者王童。这部纪录片以村民的故事为主线,勾勒出古老村庄“一步跨越千年”的变迁。柴红芳害怕上山、下山,因为当年拍摄时,每一次攀爬需要6小时。2020年,影片摄制完成,柴红芳导演真正下山时,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沙瓦村的村民们都拉着她,哭着唤她“柴妈妈”,舍不得她下山。因为这部纪录片,外面的世界看到了沙瓦村、看到了怒江、看到了中国人的不屈精神,引来了企业对村庄道路和民居改造的大力投入和支持。现在,柴导通过培训、授课,将影片的中国减贫经验分享到20多个国家,影片也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中获奖、展映。她还有一个愿望,在怒江落地工作室,通过影像的力量带动当地农文旅的发展。
《落地生根》团队的摄影记者王童,也带着很多“忘不了”的怒江人和怒江故事,继续奔赴在讲好减贫故事的征途。他带来的一张照片和一个视频,深深吸引住大家的眼睛。照片里,几位村民抬着担架上躺着的病人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视频中,沙瓦村的村民因为一台待修的冰箱犯了难,最后决定背着冰箱下山,又背着冰箱艰难地回家。这些真实客观的记录,推动当地政府和村民一起想办法脱困。沙瓦村的故事远没有结束,王童也期待着,记录下更多“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的怒江故事。
把镜头对得更准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南总站记者刘文杰分享了一个有趣的细节——这些年来,总台对怒江报道的标题画风从“苦”转“甜”了。以前报道怒江,标题里总有“艰难”“溜索”之类的字眼,现在搜索怒江,标题常常阳光明媚,比如“把好日子织成绚丽的彩虹”“一缕阳光照阳坡”。
刘文杰总结,把正能量作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相关报道的主线之一,仍是海内外报道和关注中国故事的切口。由新华通讯社、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出品的纪录片《中国减贫密码》覆盖36亿观众,被非洲、欧洲等地区的主流媒体落地播出。总之,把镜头对准基层的正能量,那些蕴含着草根的智慧,有望解答世界共通的难题。
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胡超分享的报道作品《时光相册》,可以用“一图胜千言”形容,关于国际传播视角选取的经验也沉淀其中。从背着20多斤重的书下山求学的孩子渴望知识的眼神到现在一应俱全的多功能教室,从易地搬迁的老人舍不得离开老房子“火塘”的纠结,再到车间里年轻人用心学习技能,都无声地展现着中国乡村发展过程中,人们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蜕变。这组记录时光更迭的照片,被美联社采用,也让年轻的摄影记者找寻到国际传播中的微观视角。
在日常叙事中讲述
中新社云南分社副社长张丹抛出了国际传播中媒体人都面对的痛点,国外对中国文化、当地文明的不了解而产生猎奇心理。比如,在国外的报道中,独龙族文面女的照片是媒体热衷使用的,因为代表着东方的神秘感。而她们坐飞机、涂口红、刷抖音、上直播的日常,正是今天的媒体人需要去讲述的百姓潮生活。张丹分享,独龙族妇女的金钱观之变也让人印象深刻,从以物易物的经济状态发展到愿意贷款50万元创业,反映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生代的努力和选择。
怒江融媒体中心记者王靖生感到,把怒江的故事更好地讲给世界听,当地有很多值得输送的日常片段。“我们能在时间上、空间上近距离感知怒江乡村振兴的脉搏。怒江在祖国的边境线上,我们当地人的生活,也展现了中国边境幸福的模样。我们身边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海外受众最感兴趣的、稀奇的动植物,我前不久拍摄到的鸟的照片,就被人民网日文版选用了。”王靖生说。
和年轻人一起前行
在为期3天的调研采访里,南方都市报北京新闻中心副主任潘珊菊通过几个年轻人的故事初识怒江。她说,当镜头对准教老人使用冲水马桶的社区工作者,用非遗技艺打造传统民居的民宿老板,搬迁群众在电商平台卖出第一单时的喜悦,这些年轻的乡土国际传播官就已经成为地方形象的塑造者。潘珊菊说,他们也在不断创新中国文化的出海形式,让海外的青年受众逐步了解中国,特别是让“全球南方”国家找到互鉴的路径。
贡山县融媒体中心的周颖作为一名本土的年轻记者,也在用更松弛、更潮流的方式让外界了解秘境怒江。她和同事们为独龙族文面奶奶戴上墨镜、戴上鸭舌帽,拍摄年轻人喜欢的写真,受到网友的喜爱和热评。“有一条评论我印象特别深刻,说这应该就是当下独龙族人真实的生活。这正是我们想通过镜头传递给大家的。”
本报记者 王欢 姚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