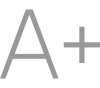柏顺文
学校古茶树研究中心的木门总衔着半缕茶香,像古韵留香的绢本,将千年茶韵晕染在当代的晨光里。
我总爱推门进去,看着蓝老师执壶时袖口漫出的青白水汽,看玻璃杯中浮沉的芽尖如何在热水里舒展成魏晋的竹简——那上面早刻满了“以茶养廉”的古训,被岁月泡得愈发清亮。
当石崇的珊瑚树在金谷园碎成奢靡的齑粉,陆纳的茶盏却在吴兴太守府盛着月光。《晋书》里那页纸还留着茶渍,写他侄子陆椒摆下十余人的酒席时,青瓷茶碗在谢安面前泛起的涟漪。“不能为我增光,反欲秽我素业!”掷地有声的斥责里,茶汤的碧色比金石更坚。彼时门阀士族的酒池肉林正蒸腾着浊气,桓温却以茶代酒,让宴饮间的觥筹换成了素色茶盏,那些被烈酒烧蚀的廉心,竟在茶烟里慢慢结痂愈合。
南齐世祖武皇帝的遗诏还带着纸页的凉感,“灵前但设茶饮”的朱批,比三牲祭品更让后世心惊。当帝陵的封土长出青苔,那杯未凉的茶却化作了碑铭——原来最高贵的奢侈,是敢于在人生巅峰保持素简。
南北朝的晨钟总与煮茶声相撞,僧人的钵盂里浮着菩提叶的影子。他们说茶能破睡,却不知这清苦的汁液更能破执。当清谈家们在竹林间挥尘品茶,茶沫翻涌如玄言妙理,那些逃避现实的士人啊,竟在茶烟里找到了更辽阔的人生旷野。陆羽在《茶经》里写下“精行修德”时,指尖一定抚过茶饼上的年轮,那是巴蜀的云雾、长江的波光,还有千万双手采制时留下的廉痕。
郑板桥的墨兰还在宣德纸上洇开,旁边的成化窑里,苦茗正熬着他的半世清名。“两袖清风”不是虚词,是他卸任时竹筐里仅有的茶种,是离任舟中随波轻晃的茶罐——当百姓捧来的茶汤在码头连成星河,这位嗜茶的清官知道,最好的政声,原是茶盏里永不沉底的清明。
而今再看玻璃杯中浮沉的碧螺春,芽尖上的白毫似是陆纳当年未抖落的茶末。从生煮羹饮到点茶斗茶,茶的形制在变,可那抹清苦始终未改。就像西湖龙井的扁舟载着宋时月光,黄山毛峰的峰峦叠着明时云雾,当沸水注入的刹那,所有朝代的廉吏都在茶汤里苏醒——他们端起的何止是茶,是“一杯清茶问今古”的叩问,是“历尽艰辛成极品”的自勉。
窗外的古茶树又抽了新芽,叶尖凝着的露珠,多像千年前某位隐士茶碗边未滴落的茶汤。在这个被速溶咖啡填满的时代,或许我们更需要坐对茶炉,看壶中活水三沸,听茶叶在杯中舒展的私语。当茶香漫过鼻翼,便知“以茶养廉”从来不是故纸堆里的陈词,而是活水新茶里永远鲜活的修行——就像这杯茶,须得经历炒青的炽烈、揉捻的痛楚,方能在沸水中释放出不卑不亢的清芬。
暮色漫进茶室时,老茶师正将新制的茶饼封存。竹箬包裹的不仅是茶叶,还有那些在茶烟里浮沉的痕迹。当我推门离去,身后的茶香追着衣角,恍惚间竟觉这清风般的茶韵,早已穿过千年光阴,在每个人的心底种下一片不谢的春山。